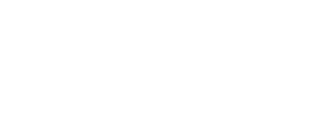道理參透是幽默,性靈解脫有文章。
兩腳踏東西文化,一心評宇宙文章。
對面只有知心友,兩旁俱無礙目人。
胸中自有青山在,何必隨人看桃花?
領現在可行之樂,補生平未讀之書。
這是林語堂在雜文《雜說》結尾用來表達他治學之道的幾句話。 這幾句話表明,他自信力很強,尤其是「兩腳踏東西文化,一心評宇宙文章」,成為他為自己立下的座右銘。 在《自傳》中,林語堂為這個座右銘作了註解:“我的最長處是對外國人講中國文化,而對中國人講外國文化。 “眾多學者和廣大讀者,也大都以此來品評這位國學大師學貫中外,融合中西文化的。
樹有根,水有源。 林語堂之所以能成為一代國學宗師,融通東西文化的世界文化巨匠,是與他兒時所受的發蒙教育關係很大。 林語堂生於1895年(光緒二十一年),時值清末。 在《八十自敘》中,他說:“我生於福建南部平和縣的坂仔鄉(漳州龍溪)。 下列幾件事對我童年影響最大:一,山景。 二,家父,不可思議的理想主義者。 三,親情似海的基督教家庭。 “又說自己”是一個十足的鄉下人“。 正因為,林語堂童年的家庭生活融合於中西文化,家庭關係又是中國式的,受中國傳統文化的浸染較深,尤其是其父對子女進行中國傳統文化開蒙教育十分重視。 這就為林語堂日後成長為譽滿世界的文化名人打下紮實的基礎,也就是說在坂仔鄉間他就練好了“兩腳踏東西文化”的“童子功”。
林語堂父親林至誠,年輕時沒機會讀書,走不了科舉入仕之路。 但閩南農村耕讀文化盛行,他懂得讀書的重要,靠自學略懂詩文,能寫粗淺文言文。 他既是鄉村牧師,又是家庭教師,自己走不了“讀書為官”之途,就把希望寄於兒子身上。 林語堂回憶說“他教我們古詩、古文和一般對句。 他講解古文輕鬆流利,我們都很羡慕他。
《易經》說:“蒙以養正,聖功也。 “中國人歷來重視對兒童進行啟蒙教育。 通過啟蒙教育,使兒童自幼扎下中國傳統文化之根,從而形成初始之自然觀、道德觀、歷史觀、倫理觀、價值觀,而這種教育通常在書館、村學、家塾、鄉學、義學、社學等名稱不一的處所進行。 為實施這種啟蒙教學而編成的讀本,統稱為蒙書,蒙養書、蒙童讀本或蒙學教材。 明清時期,作為蒙養教材,一般是選用《神童詩》《百字姓》《三字經》《千字文》《弟子規》《四書五經》《幼學瓊林》《聲律啟蒙》等,有一定文化基礎的家長有時還會自選教本。 林語堂的父親除了用《四書五經》《幼學瓊林》《聲律啟蒙》之類的蒙書教授子女外,還特地選用《鹿洲全集》作為子女學習古文和傳統文化的必讀書。 清末,《鹿洲全集》在閩南地區流行,著者藍鼎元,字玉霖,別字任庵,號鹿洲。 康熙十九年八月二十七日(1680年9月19日)生於福建漳浦縣赤嶺鄉,雍正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(1733年8月1日)卒於廣州任內,享年54歲。 康熙間隨族兄入台參贊軍務,雍正元年(1723年)以優貢入選進京,參與修纂《大清一統志》。 五年,雍正帝召見,條陳治理臺灣、河漕、海運、兼資、鳳陽民俗土田和黔蜀疆域六事,為雍正帝所賞識。 未幾,授為潮州府普寧知縣。 到普寧上任不久,又兼署理潮陽縣。 后因政績顯著,升任廣州知府。 《清史稿》將他列入循吏傳,說他“善治盜及訟師”“聽斷如神”“斷獄多所平反,論者以為嚴而不殘”。 舊《潮陽縣誌》說他“有包孝肅複生之稱”。 更為可貴的是藍鼎元一生向學,是位著作面頗豐的道德文章名重於世的大學者。 林語堂父親對藍鼎元十分崇拜,對《鹿洲全集》愛不釋手。 他不僅把這部書作為兒子的童蒙必讀書,而且要求孩子們有些篇章能熟背。 上世紀八十年代末,吾師黃典誠教授曾談起與林語堂的二哥林玉霖先生同居一舍。 林玉霖告訴他,其父平生敬重鼎元之為人,不僅將《鹿洲全集》作為家人子弟必讀書之書,而且將自己的名字也取用鼎元之字,叫玉霖。 後來,林語堂及其四位哥哥都成為文化人,也是因為自幼受父親的此種蒙養,埋下了中華傳統文化壯實的種子。
藍鼎元官階不高,治政時間也不長,可在當時以及身後名氣卻相當大,曾被列為清代數百名人之一。 《清史稿》有他的傳記,尤其是在臺灣及閩廣影響更大,地方誌書大都有他的事蹟介紹。 最近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輯臺灣先賢先烈傳,也有鼎元其人。 《辭源》《中國歷史人物生卒年表》《中國文學家大辭典》等,都有他的名字。 藍鼎元不僅是一個地方性的人物,也是全國性的名人。
藍鼎元從一個農村的苦孩子,成為全國性的名人,靠的是自強不息的奮進精神和名師的教誨。 他一生勤於著述,著作等身。 他的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著作《鹿洲全集》中,被譽為經濟大儒、文章巨匠,學適於世用,而志乎世道人心,心系乎生民社稷,詞不浮誇,論切人情物理。 故其著作備受史家的讚賞,收入於各種藏書。
《鹿洲全集》行世很早,並屢經再版。 據悉最早有雍正十年(1732年)刻本,至光緒六年(1880年)七世孫藍王佐再補刊本,閩漳素位堂代印本。 林語堂兄弟幼時讀的可能就是這個版本。
《鹿洲全集》收錄鼎元書稿八種,內容有:《鹿洲初集》凡20卷,分為書、序、傳記、論、說、考、賦、檄、銘、箴、讚、事錄、讀傳、書後、跋、壽文、告文、祭文、哀辭、行狀、墓誌銘、墓表等240篇文章,內容廣泛,是專著以外的文集彙編。
《女學》凡六卷,為女學之專著。 康熙五十一年(1712)寫成,在時間上是最早完成的一部專著。 “天下之治在風俗,風俗之正在齊家,齊家之道當自婦人。” 該書纂組古訓,大致與《小學》相近,而編輯等較《小學》更見苦心。 所謂「扶倫教之傾,舍此是編而奚屬哉。 ”
《東徵集》凡六卷。 清康熙間臺灣朱一貴之役從軍時所作。 該書通過親自實踐與考察,對如何經理臺灣提出諸多很有見地的主張,被譽為“籌台之宗匠”。
《平台紀略》凡一卷。 離台後於雍正元年在家鄉寫的,這是一部平定朱一貴起義的紀實文章,是為補充《東徵集》之不足和糾正當時的一些錯誤傳聞而作。 事關台事,後人治台者,《東徵集》和《平台紀略》是必讀之作。
《棉陽學準》凡五卷。 他任普寧知縣時創建棉陽書院,該書是他講學棉陽書院的著作,併為書院制定同人規約、講學規儀,所謂“得濂洛真傳”。 四子、六經、近思錄、小學而後所未見者。
《修史試筆》凡上下二冊。 這是鼎元“欲寫宋史,而以此為試筆也”。 他認為「宋史繁蕪」,必須「釐正,而欲更修之」。。 試筆內容是以唐代較有作為名臣,“擇其忠節,經濟之炳乾坤者,列為傳名”,凡35人,又五代一人。
《鹿洲公案》凡上下二卷,為潮普邑令時治獄紀述,列舉20多個案例,讞析疑獄,鉤致出奇。 他持正無畏,疾冤如仇。 史家評他「長於斷獄」,“有包孝肅複生”之譽。
《鹿洲奏疏》凡一卷六條。 為履歷奏條、經理臺灣、臺灣水陸兵防、漕糧兼資海運、鳳陽民俗土田、黔蜀封疆,是他向雍正皇帝奏疏輯錄,內容均多見地,如遵義由四川改為貴州轄屬,就是他的建議,並立即得到批准更改。
《鹿洲全集》內容涉及到政治、軍事、經濟、文化教育、商貿、交通、少數民族政策以及文學、史學、地理學和哲學等等,知識很淵博。 他的著作能得到重視,首先是他的思想觀點符合當時政治標準,他奉行的儒家學說,闡發治國平天下的道理,但他又不同一般只讀聖賢書的儒生之輩,他事事從國家大事出發,處處以民族利益為重,敢於堅持自己正確的主張,不計個人安危得失,故能根據當時的國情抒發自己的政見。 經世濟民的「經濟文章」是他著作中的一大特色,也是他的成功之處,所以他的著作具有生命力。
《鹿洲全集》收錄的《鹿洲初集》,是較早刊印行世的。 福建巡撫張伯行在康熙四十八年(1709年)已醜秋日,在《鹿洲初集舊序》中寫道:“閩中漳浦,稱山海奧區,人文淵藬。 余蒞閩,莆下車,創書院於會城,招九郡同志,講明正學,纂修先儒諸書,而漳浦之才為獨盛。 藍生玉霖,八閩翹楚也。 少孤,嗜學,長有文名,當道廉其品,鹹折節推重,生閉戶著書,自豪岸然,不以為意。 …… 蓋根本深厚,氣魄力量無所不達,而謹慎小心,深之以涵養,斯誠經世良才,吾道之羽翼也。 “”昔范文正公作秀才,便以天下為己任,觀生之文,可知生之志哉! 生長文獻之邦,道南一脈,代有傳人,使微言大義,與日月經天,不絕長夜,余所厚望於生者,生曾知之乎! 漳浦東溪,陳剩夫,周翠渠,黃石齋諸先生,皆卓然有立,增光宇宙。 “作為對藍鼎元有知遇之恩的師長,張伯行對藍鼎元的為學做人之道和著書立說,予以很高評價,同時也提出厚望。
與藍鼎元同時代的名士汪紳文,於康熙六十年(1721年)在給《鹿洲初集》寫的序中,稱讚“藍子玉霖,奇士也,志高識遠,超然塵埃之表,議論風采,悉奉古人為師。 作為文章,原原本本,可以坐言起行,功深於鎔經鑄史之中,而氣磅礴於語言文字之外,斯人與文而皆奇。 昔太史公行天下,周覽名山大川,故其文疏蕩有奇氣。 今藍子年方壯,行將遍歷乎四海九州之大,與其賢人君子交遊,志氣激昂,精神煥發,造詣正無可量,區區集中數藝雲乎哉。 “”藍子一經生耳,獨能於人心風俗之所維繫,綱常名教之所昭垂,天經地志之所研究,勤勤懇懇,剖晰精詳,不啻三致意焉,此豈經生之文乎。 余故曰:玉霖奇士也。 “他把藍鼎元與太史公司馬遷類比,高度評價藍鼎元功深經鑄e史,為人為文皆奇。
由此可知,林語堂之父將藍鼎元的《鹿洲全集》作為子女的蒙養必讀書,並選定某些篇章背誦,是獨具慧眼的精心設計。 林語堂兄弟們受益於蒙養良多,尤其是受益於《鹿洲全集》,讓他們銘刻於一生記憶之中。 林玉霖曾說,其父以《鹿洲全集》為家人弟子蒙養必讀之書,使「乃弟語堂異日之得以馳騁文壇」。。 這種說法,在林語堂諸如《國學拾遺》等許多著作中得到印證。